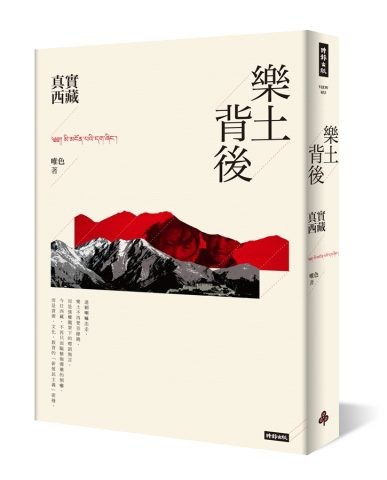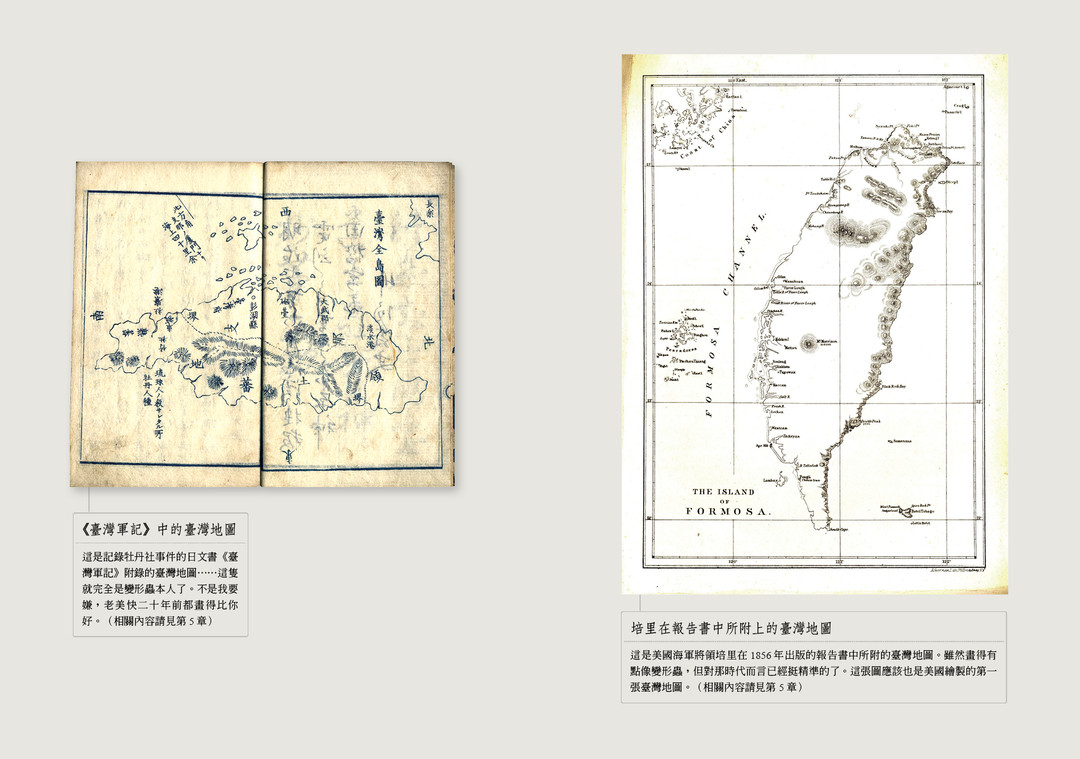文/丁學良
本文是應《新新聞》之約,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起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怎麼用了以上的標題,扯上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在玩東北式的忽悠?玩香港式的搞笑?還是玩台灣式的八卦?
- 那破天荒的劇烈一步
都不是。本文是認認真真的回憶和反省,是誠誠懇懇的感激和傷懷,是趕在「不要太晚了!」之前的為史作證,哪怕這並不是官方正史,只是草民的個人經歷。
「文革」在我那一代少年學子的記憶裡,是始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兩點鐘──學校裡的擴音喇叭宣布來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從現在起,一律停課鬧革命。何時復課,等待中央的有關指示。當時挺開心的我,初二年級尚未完,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從那一天起,我們就一步跨進了橫掃人類各種文化遺產的狂飆時代,其中又以「大破四舊」即剷除中華傳統精粹為烈。
從那一時刻開始,我成了母校安徽省宣城中學的全職革命學生,一直鬧到一九六八年的年底。期間幹過正宗的紅衛兵小將應該幹的所有的文攻武衛、壯懷激烈,只差沒有殺死人和沒有被人殺死。可那也不是有意拒絕為之,而是碰巧沒挨上。凡此種種,我的《革命與反革命追憶》(聯經公司,二○一三年七月增訂版)裡有細細交代,此處不再贅言。
毛澤東一聲令下,我們紅衛兵於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始,被分批驅趕到農村裡接受再教育。雖然我們很快就明白了,「偉大統帥」的這個「你們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是蒙人的花招,但還是陸續發現到,在偏僻的鄉下確實有令我們大腦開竅的少數幾樣際遇,其中一樣就得益於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時的安徽南方農村,實行的是生產隊「大呼隆」作業:每天清晨村裡的大喇叭一響,我們就得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拿農具、排成隊、唱著毛主席語錄歌走到田地裡,集體作業。每天都要勞作到天黑,十幾個小時,吃也吃不飽,累得精疲力盡。唯一的精神補償品,就是偷偷收聽發自台灣的「自由中國廣播電台」。
農民隨身帶著一部手提式電晶體收音機,是「黃山牌」,有幹部在場時,就調到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頻道,收聽革命樣板戲。沒有幹部在場,就調到台灣的廣播頻道,收聽「敵台」。
- 由收音機聽見台灣「敵台」
我們知識青年一開始,被農民嚇得不輕。
「收聽敵台」是「文革」中的一樁嚴重反革命罪行,在城裡有很多人就是因此而被抓住、判刑、坐大牢的。在距離宣城縣城二十公里的安徽勞動大學裡,一位躲在宿舍裡吃西瓜的教師,因為朝搪瓷臉盆裡吐瓜子發出的「滴答、滴答」聲響,被窗外的群眾專政大隊隊員誤以為是收聽「敵台」,就把他抓起來,關押審問。而在偏僻的鄉村裡,農民們就敢在田地裡公然這麼幹!
他們大部分時候收聽的不是台灣政戰系統編制的政治節目,農民不太聽得懂;他們最愛聽的是中國傳統戲曲,他們稱作「老戲」。這類老戲在民國時代是皖南農民們過年過節、紅白喜事期間必有的重頭項目,年紀大一點的,都還能有板有眼地哼上幾句。
可惜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季以後,就完全被禁了。農民們覺得革命樣板戲差遠了,沒味道。起早摸黑,臉朝黃土背朝天,他們能聽上幾摺子老戲,也算是靈魂裡補了一點氧。
像我們這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少年一代,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認知,原本是絕對的負面。每日每時中共宣傳都要把台灣描述得比人間地獄還糟糕,是美帝國主義庇護下的罪惡淵藪。可是跟在農民後面時常聽幾段傳統戲曲,再加上夾在其中的播音員短短的「對大陸同胞」的溫馨問候,不知不覺的,就大大降低了對台灣的敵意。
腦子裡時不時地會疑問:那邊的社會沒那麼糟糕吧?他們能把中國傳統戲曲保留的完整無損,也算是一樁善事吧?
- 連老毛也愛聽「老戲」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毛澤東和他的最可靠的文革助手,私下裡的看法與皖南農民們是一致的。治中共黨史的名學者高華先生,十幾年前就跟我談到,「文革」發動之前毛澤東授意,要把最精華的中國傳統戲曲請最優秀的藝人演唱,錄製下來,他本人還想欣賞。
中共理論部門編撰的史料處處顯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首席顧問康生,一直就是個老戲迷,且堅持要看未經過「清潔」處理的原版戲曲,愈鹹濕愈過癮(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內部版)。
也是多年以後(一九八九到九○年間)我才知道,蔣介石為首的黨國高層,主要是為著在台灣社會和國際舞台上凸顯,他們領導的國民黨才是中華正統,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是中華傳統的毀滅者,便發起一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利用文革事件來支撐國民黨統治的道德基礎(陶涵:《蔣經國傳》,台北:時報出版,二○○○年版第十七章)。
- 在遙遠的外國認識故國
我從皖南農民收聽「敵台」的小視窗那兒獲得的關於中國傳統文化被中華民國在台灣精心呵護的初步印象,一直到文革以後被選中赴美國留學期間,才有了機會擴展、深化和具體化。我留美的第一站是匹茲堡大學,那裡有楊慶堃、許倬雲等學界前輩和一個小小的東亞圖書室。在那兒的一學年(一九八四年九月至一九八五年六月),使我多少能聽到、讀到未被中共歷次革命動過手術的中華文史資訊。
緊接著在波士頓的八年,無比豐富的機會和資源,為我開拓了認知正版的中華傳統及其蔓延和轉型的種種情境。與張光直和余英時等大師輩的交往、參加頻繁的「燕京學社」漢學研討會、跟來自台灣的幾代知識分子對談、閱讀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裡的完整系列文獻,加之隨後應聯合報系邀請訪問台灣與文化界、教育界、傳媒界、政經界、宗教界、工藝界的親身交流,讓我終於接駁上那些在中國大陸被生生切割了的中華文化淵源,與傳統中國通電了。
每當我和上述的人、書、事深度接觸的時候,都很自然地把他們和它們假設性地納入到文革那道洶湧紅流之中,發出一連串的傻問:倘若他們和它們都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便能熬得過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批判胡風集團運動、反右運動、大饑荒等等,還有可能熬得過文革嗎?
我翻閱漫長的「文革中受害的著名知識分子名單」、「文革中被毀壞的歷史文物一覽」,看來看去,他們熬得過去的概率接近於零,它們則稍高一點。
所以,上面的連串傻問也可以翻譯成直白的話語:諸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思亮、王寵惠、李濟、董作賓、台靜農、梁實秋、乃至林語堂、錢穆、徐復觀等等,倘若當年拒絕移居於中華民國在台灣,而是和陳寅恪、熊十力、陳夢家、張東蓀、老舍、傅雷、翦伯贊、梅汝璈等等一樣,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不就成為後面這群文化人一樣的「生也苟且,死也白死」的黑九類了嗎?想想真後怕,為他們及其家人、也為他們的幾代弟子捏一把汗。
- 文化中國的祭壇在台灣
所以,不管大家如何看待蔣介石為首的那兩代中華民國統治層在政治領域裡的所作所為,也不管大家如何看待今天的國民黨之人事和政策的走向,凡是對中華文明有真心認同的人士,都得承認,一九四九年以後、特別是一九六八到七七年期間的中華民國,為保留華夏傳統做了許許多多值得今人和後人感激的善事。
你可以抨擊他們在海峽這邊是為著政治目的打弘揚傳統文化的牌,但這比海峽對岸的毛澤東集團為著政治目的摧毀傳統文化要好過無數倍。尤其是對我這樣親歷過文革的大陸學子,每次對比一九四九後三十年左右長時段裡海峽兩岸的學術出版物和媒體的文化記事,都不得不重申一句:「文化中國」的祭壇是在台灣,而不是在中國大陸。
「文化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特別是在全球華人圈裡,贏得了厚實的尊重和誠摯的感謝。雖然當初(一九四九至八八年)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執政者們並沒有現今「軟實力」之類的概念,但他們推展的傳統文化政策,卻客觀上釋放出軟實力的效應。直到他們去世之後多年,每當海峽兩岸一大一小兩個政體發生衝突的關頭,環球華人社群多半是把同情心投向小的一方。這一是拜台灣民主化掙得的回報,一是拜台灣遺存了更多的中華文化傳統贏得的回報。
以上的話語,筆者早先也在其他的時間空間裡言說過,可眼下說來,卻別有一番意緒。恰逢文化大革命發起五十周年,在海峽那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地上,無數的人們亟想議論,卻不讓議論。在海峽這邊的中華民國領地上,絕無勢力禁止人們做任何議論,卻罕有人萌發議論的興致。
若是十數年後,「文化中國」的情懷也被台灣大多數居民所拋棄,「文革」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之類的大事件,恐怕海峽兩岸都缺乏議論之聲了。不過到了那時,固執己見的筆者仍然會不甘寂寞,偏偏要把本文的要旨大聲重複一遍:
- 感念大浩劫裡的中華民國
中土禮崩樂壞、天下大亂之際,孔夫子呼籲:胸懷「悠悠乎文哉,吾從周」的仁人志士們,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這被毛澤東江青手下的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怒斥為「妄想大開歷史倒車」的反動主張(《論法家和儒法鬥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自一三二至一三三頁)。二十世紀中後期,中華民國在台灣所做的,至少大大有益於後兩項──在中國文化大浩劫的歲月裡,盡力護衛中華傳統文化,提供此一傳統為數不少且惶惶不可終日的代表人物以棲身續命之所,客觀上為華夏的文化道統延續了幾支香火。
僅僅為此,我等學子也不會忘了中華民國在台灣!
(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專長政治社會學)
(本文由新新聞授權轉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延伸閱讀:
文化大革命結束 40 周年,這座「文革墓園」記錄下了中國政府的沉默與難堪